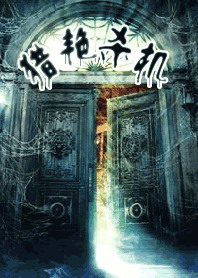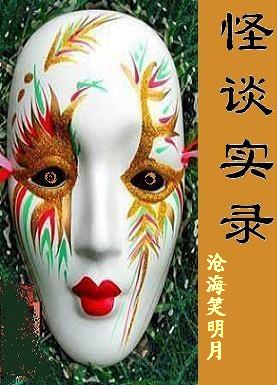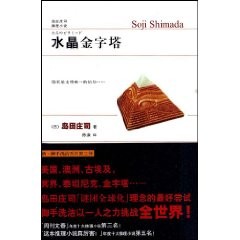小翠之死猎手静静的在露台趴着,楼下足球赛转播的声音震耳欲聋,他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一会儿,他有他的最佳娱乐。想到这里,他的心又开始剧烈的跳动。他再度设想着玻璃窗里面的翠翠在干什么,这是他起的名字。因为翠翠总是穿一件豆绿色的紧身T-SHIERT,对于农村姑娘,她打扮的一点儿不土气,而且她还在努力的改变自己的乡音。猎手对这一点非常欣赏。每次他到翠翠所在的饭馆吃饭都会发现翠翠的进步,他想今天是犒赏翠翠的时候了。不知道一会儿翠翠会是什么样的眼神,他喜欢大眼睛的姑娘。 翠翠的房间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她要抓紧时间洗澡,另一名休息的女孩儿刚洗过澡和男友出门了。一会儿合住的另六名女孩儿回来,只有一个洗澡间的房子住了八个人,翠翠一定不会浪费这个时间。...
二十年前,这片大陆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各个家族都很友好,并没有敌我之分,都在共同地领导着片大陆走在美好的世界道路上。但好景不长,在一次罕见的天文灾害,世界上没有一处角落有阳光,整片大陆都处于黑暗状态。就在这时,魔王趁着光明不再而从黑色地带降临,违反了和平条例,试图侵略并统一大陆。大陆的人都努力地抗战,但由于出现了让人发指的内奸,和战斗力上的悬殊,最终,各大家族首领不得不签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人们都非常不满,甚至直接称它为——投降。有不满就有反抗。签下不平等条约后,仍有一部分不惜脱离家族去反抗的人,被幕府称为恐怖分子。在反抗两年后,大部分恐怖分子组织都已瓦解,而其中还是有一部分“顽固分子”在组织新的反抗组织,斗争从未结束。...
前言(1)当某人宣称自己与上帝共度了整个周末,而且是在一间棚屋之中,谁会相信呢?然而这就是《棚屋》的故事。 从去田里帮邻居捆干草喂两头奶牛算起,我和麦克相识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那会儿,我和他就像当下孩子们所说的,总“厮混在一起”,同喝一杯咖啡,或者我来一杯热腾腾的印度拉茶加豆奶。我们俩谈话时感到由衷的快乐,笑声不断,偶尔也会感动得掉下一两滴眼泪。坦率地说——要是你懂我的意思——我们越老越喜欢混在一块儿。 他全名叫麦肯齐·艾伦·菲利普斯,大多数人都叫他艾伦。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男人最前面的名都一样,通常人们称呼中间的名。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有装腔作势之嫌的“一世、二世、三世”或“老麦肯齐、小麦肯齐”等称呼。对于自称朋友来套近乎的电话推销员,这个法子倒很有效。所以他与祖父、父亲以及长子一样,拥有指定的名字“麦肯齐”。关系普通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唯有他的妻子南,以及一些极...
天色初明,晨雾朦胧,陆宸拿了一摞手抄经欲往山头玄古寺。 刚小步踱出山庄后门,就见左旁的废旧石室外有白影左右飘忽。瞧那身量和匪夷所思的行事之风,他觉得陆华庄里大约找不出第二个来。 从玄古寺折返已是一个时辰后,陆宸余光扫见那白影还在探头探脑,忍不住也望了几眼。那是间大石垒成的屋子,墙角爬满青苔,屋顶挂着沾灰的蛛网,除了面积颇大,实在瞧不出其他特别。 他上前一拍白影肩头,“大清早跑后门瞎琢磨什么?” 白影依旧直勾勾的盯着石屋看,不走心反问,“一去一时辰,是藏了哪家美人在山里?” 陆宸好气又好笑,“陆漪涟,说话要凭良心。玄古寺里头摆的可都是列祖列宗,再几日又是爷爷忌日,我能蠢到把美人藏上头。”说完,觉得蹊跷,回头向山道一望,怀疑问,“方才你看见我了?”...
那么罗兰到底是谁?他的世界在转换之前又是什么样?黑暗塔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追寻黑暗塔?对此我们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毋庸置疑,罗兰是武士一类的人物,责任就是保护(甚至可能救赎)那个在罗兰记忆中“充满了爱与光明”的世界。但是罗兰的记忆到底有多符合真实情况还是个问题。 我们知道的是他在发现自己的母亲与马藤——一个比沃特更强大的魔法师——有染之后而被迫提前经受了成人考试;我们知道实际上是马藤在暗中策划了这一切,希望罗兰无法通过成人考试而被“发配到西方”的荒原;我们知道罗兰最后通过了考试,让马藤的阴谋功亏一篑。 我们还知道枪侠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有着某种奇怪而基本的关联,人有时甚至有可能在两个世界中穿行。...
50年前,长沙镖子岭。 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 铲子头上带着刚从地下带出的旧土,离奇的是,这一坏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血液里蘸过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接着道,“下面是个血尸嘎,弄不好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撂在下面噢。” “下不下去喃?要得要不得,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独眼的小伙子说,“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你屋里二伢子海式撩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只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
酒鬼的醉话还记得卜天一第一次喝多扒在我肩膀上如是叨叨:实在很难说清这种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我打小就有的一个怪癖……谁记得清是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呢?反正这怪癖让我的大脑不停的进行一些异常工作,直至今日,终于让身旁亲近的人不得不统一说辞对外称我“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就是这么的“于众不同”吧!我从没有做过“美梦”,尽管那个梦么是见天的做,但如梦的景况万变不离其宗——幽灵、恶鬼、魔怪、妖精、僵尸、吸血人蝠……和更多不知名的恐怖种类打定主意要做我的梦境常客,不请自来的总是擅自闯入我的夜眠世界,而我从小时候总是对人的吓到虚脱尿床后吵醒了全家陪我猜谜语,锻炼成了见惯不怪没了反应,反正不可能不睡觉吧,反正天亮了总会醒吧。...
序言仅以此文献给在祖国广袤大山中艰苦奋斗过的老一辈地质勘探工作者。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引子 如果我在四十年前的当时,带着那只胶卷盒,立即原路返回,顺着水势逐渐低落的地下河离开,那么以后的一切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然而,在黑暗的地下河上,我们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决定是否正确, 但是我相信,即使时光倒流到那一刻,我还是会作出相同的选择。 性格决定着命运。 第一章 航拍 1962年与1963年的交汇,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想必很多人都有记忆,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大跃进”悄然结束,中印边境的战争局势已经明朗,很多人都以为混乱的局面已经过去,国内会迎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