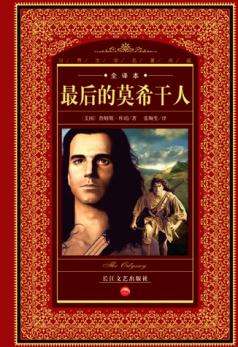【故事简介】 【作者简介】 朱秀海,海军创作室创作员,一级作家,满族,1954年生于河南鹿邑,1972年12月入伍,曾先后在武汉军区、第二炮兵和海军服役,两次参加对越作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院士。 《乔家大院》 作者:朱秀海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ISBN:7532619257 出版日期:2006年1月 市场价:30.00 元 目 录 序 第一章第四十章 后记(一) 后记(二) 附录一 晋中乔家大院 附录二 相关资料 序 在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时创作的电视脚本,就像“庄周化蝶”抑或“蝶化庄周”那样,几经“磨难”,几度“蜕变”,终于以全新的体例编撰完成,即将付梓。...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见背[1],两易春秋[2]。冤酷日深[3],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4],以报大仇,恤死荣生[5],告成黄土[6].奈天不佑我,钟虐先朝[7].一旅才兴[8[9]],便成齑粉[9],去年之举[10],淳已自分必死[11],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12],菽水之养无一日焉[13]。致慈君托迹於空门[14],生母寄生于别姓[15],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16],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呜呼!双慈在堂[17],下有妹女,门祚衰薄[18],终鲜兄弟[19]。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於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20],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
江南晚报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离开上海,到青岛的山东大学执教。这是他生活沉静,精力旺盛,创作多产的时期。青岛的山东大学花木掩映,景色宜人。授课之余,他常常独自走出校门,沿着海岸走过浴场、炮台、海湾石滩,看浪花翻腾,云起云飞。面对大海,面对自然,激发了他更多的写作热情。1933年夏,沈从文偕未婚妻张兆和到青岛崂山游玩,在风景秀丽的一条溪的对岸,他们看到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孝服,在岸边哭着烧了纸钱,便在小溪中汲了一罐水,提着回去了。这一个看起来十分寻常的情景,勾起了作家对故乡一种“起水”的古老习俗的联想。在湘西,当长辈去世时,小辈要到附近的河里或井里去取一些水,象征性地洒在死者脸上身上,表示洗净他在尘世间的污垢,进入天堂。看着这位孝女远去的身影,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他准备根据她写一个故事。不久,他回到北京便与张兆和结婚,定居于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因院...
第1部分海滨城市的道别灵站在车站月台手扶着油漆脱落的栏杆昂望着天空.天空澄澈湛蓝仿佛与这个城市接壤的海面,灵的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久久的挂在眼眶的边缘,她在强忍着不肯让这包裹着细碎幸福的泪珠跌落,落下了,就会摔碎。汽笛 鸣,又一辆列车呜咽的从这里开走,带着旅途奔波的人们。“霄,我将要走了,离开这里了”她转过身来背靠在栏杆上低头说道,双脚在地板上划着圈。“你也该走了,希望你这次在这个城市的旅行是快乐的”我走上前一步帮她把行李放在身边,“你还要不要带些什么?”,我不敢去看她的眼睛。灵儿要结束自己的旅途,告别这个湿润文气的海滨城市,候车厅里响起了催促旅客上车的提示,她手持车票上了那辆即将启程开往一个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的城市。...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长江文艺出版社前 言早在几年前,就有朋友建议我写马俊仁。朋友说,马俊仁是中国当代风云人物,在世界也很知名。他在国内外各种田径大赛中,拿到了不计其数的金牌银牌铜牌。说他是个伟大的田径教练,也许并不过分。朋友又讲了很多理由,包括马俊仁的传奇色彩,以及马俊仁在这些年中引起的种种新闻和争议。大概总有一些说法触动了我,使得我多少开始注意这个选题。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有朋友再次向我推荐马俊仁这个人物。他们说,马俊仁当下处境和心境都非最佳。多年来,很少有人像他受这样大的冤屈,而他特别需要方方面面包括舆论对他的理解和呵护。朋友的用意很简明,希望马俊仁的处境和心境能多少改善一下,那他一定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再为中国拿几个金牌。...